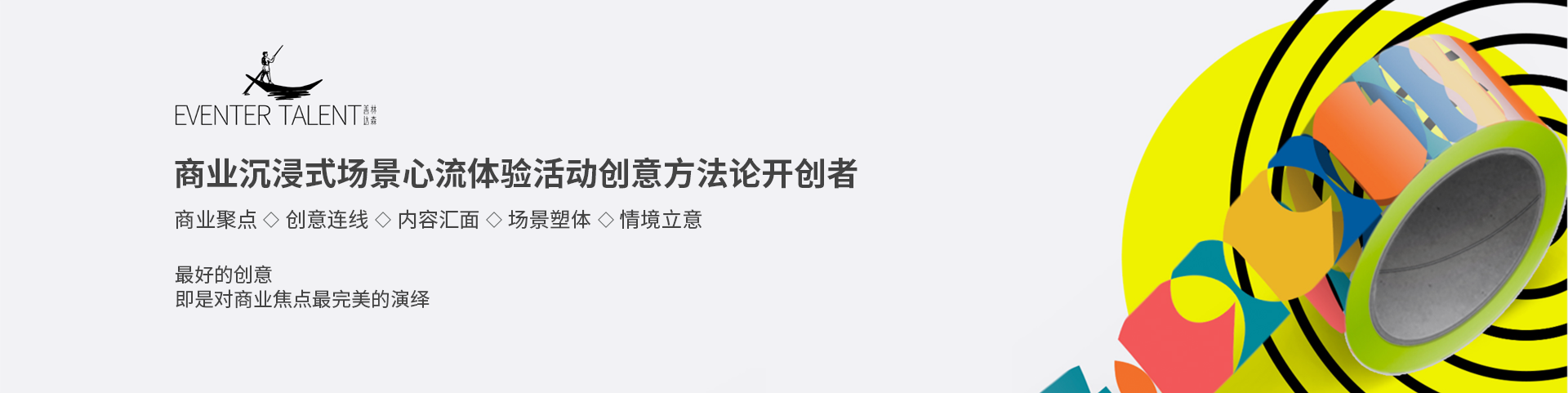
民族運動會留下的思考
2013-01-12 12:13:21
第九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9月18日在貴陽落下帷幕。在9天的時間里,55個少數民族的6773名運動員參加了16個大項的競賽和185個項目的表演。熱鬧的運動會之后,也給人們留下了諸多思考——
傳承之道:
民族傳統體育需要靈魂支撐
第九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以下簡稱“民族運動會”)中,不管是重在力量與技巧的競賽項目,還是重在審美與意境的表演項目,都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熱鬧”成為本屆運動會淡化“金牌意識”后最直接的體現。民族運動會期間,主辦方專門組織了對獲得民族體育論文征集優秀獎的頒獎,多位專家、學者就民族體育在社會轉型期的傳承和發展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研討。
長期從事民族體育研究的衡陽師范學院教師田海軍用“經濟發展羽翼下的文化軀殼”來形容部分民族體育項目的生存現狀。他說,推動民族體育發展不能只注重文化的依存形式,而忽略民族本質文化的自然基礎和人文基礎,否則,民族文化的基因就會突變或者丟失,民族文化就會滅絕,民族體育文化作為傳承民族文化的形式也將不復存在。
上世紀90年代,中國的體育學專家經過整理,驚訝地發現:中國民間保存著1000多個傳統體育項目,其數量堪稱世界之最,而其中有700多個體育項目來源于55個少數民族。當中國已發展成為奧林匹克運動的大國時,體育專家在源遠流長的中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中找到了原生性的本土體育資源和體育精神。然而,活動策劃,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和社會轉型,民族體育的發展同樣面臨著嚴峻的形勢。貴州財經學院教師何小紅等人在調查中就發現,民族體育十分豐富的水族,傳統體育項目已經失傳或正處于失傳的邊緣。而新疆早些時候有約600項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如今也只留下278項。
在本屆民族運動會的眾多表演項目中,有部分節目已經很難在少數民族的現實生活中找到它的原型,其藝術性、娛樂性顯得更加突出,而民族傳統體育最為根本的“民族性”卻在悄然淡化,民族傳統體育的靈魂正在喪失。
推廣之困:
民族的,還不是世界的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這句話幾乎耳熟能詳。縱觀第九屆民族運動會,雖然不失為一屆成功的賽事,可還是不免讓人感嘆:“民族的,還不是世界的。”
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多與勞動生產活動密切相關,而中國又因幅員遼闊、民族眾多,使得各地、各民族的傳統體育項目呈現出形式多樣、富于地方色彩的特點,但這也就難免造成“此民族創造的運動項目,彼民族并不適合”的局面,因此中國傳統體育項目,目前“各自為戰”的現象非常普遍,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其普及、發展之路。
據了解,在內蒙古發展良好的摔跤運動,到了其他地區卻出現“水土不服”:民族傳統、身體條件等因素,導致民族摔跤在其他省份很少有人參與。因為參賽需要,很多省市會在賽前臨時聘請內蒙古“外援”。對此,內蒙古代表隊主教練查干扎那表達了他的擔憂:“如果只有內蒙古一個地區在發展這項運動,這樣下去,民族摔跤如何走向世界?”
如何使民族傳統體育項目走出狹隘的民族地域,向全社會推廣,是民族體育能否繼續生存發展的關鍵。可喜的是,目前有些民族體育項目,已開始走進尋常百姓的全民健身生活。
重慶市石柱土家族自治縣將擺手舞、板凳龍、竹齡球等民族體育項目列入全民健身計劃,目前參加此活動的老百姓已有10萬人之多。而在云南省景谷傣族彝族自治縣,城鄉共有陀螺場地216塊,縣城的幾十塊場地從早到晚都有人打陀螺,幾個用打陀螺運動戰勝了疾病的老人成了推廣陀螺項目的活廣告,打陀螺已成為當地名副其實的全民健身項目。寧夏涇源縣正在探索將回族傳統武術踏腳套路進行整理,作為廣播體操在全縣推廣,而在寧夏南部山區,一些地方已經自發地將民族體育項目作為趣味運動項目,納入當地的農民運動會中。
這些成功的案例絕非偶然,它為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發展指明了一條可供參考和借鑒的路徑。
開發之策:
民族絕技如何“生財有道”
“高空王子”阿迪力和他所擅長的達瓦孜早已蜚聲全國,他成名后最高出場費曾高達200萬元,但當初初次的出場費只有62元。通過市場化運作,阿迪力不僅名利雙收,更讓這一祖傳絕技名揚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