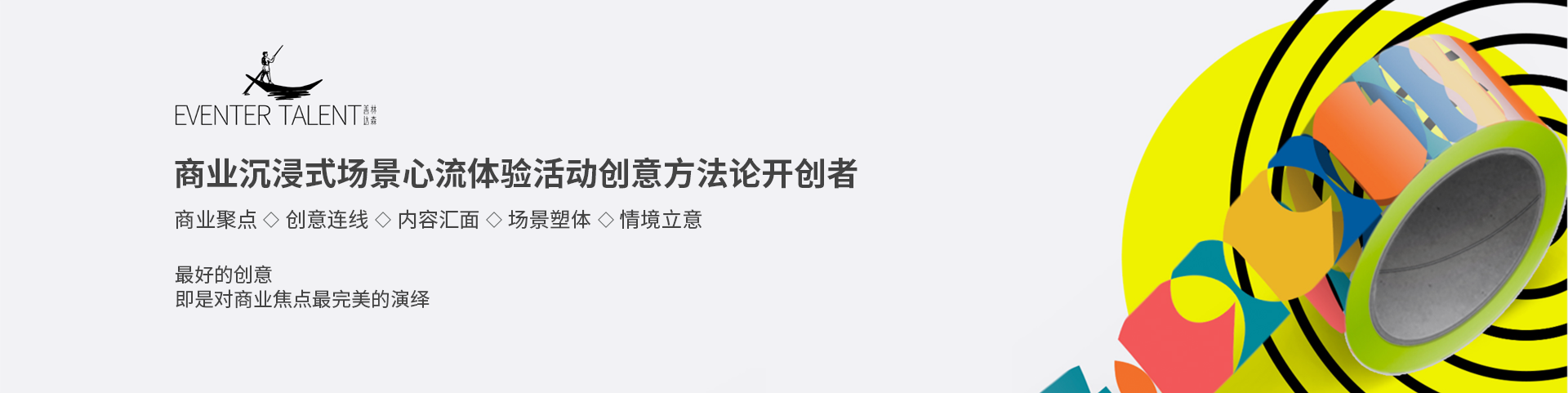
上海公關公司:評論:和諧社會與工會理論創新
2013-04-09 13:00:14
現實生活中,每當說到勞動者的種種弱勢情況時,學術界的人士比較喜歡提出的一個質疑是,中國的工會哪里去了,為什么中國的工會組織不發揮作用?似乎指出工會的問題,學術界的責任就算盡到了。實際上,稍稍反思一番就知道,我國工會作用不盡人意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在學術界。翻翻我們某些學科的教科書,與工會組織相關的內容,不是在“妖魔化”工會,就是在片面宣傳工會,明顯脫離實際,給人誤導。為證明此言不虛,特舉例說明如下:
首先看近二十年來的顯學——經濟學。眾所周知,在我國的經濟學教育中,西方經濟學是顯學中的顯學。中國這二十多年培養的數以百萬、千萬計的學子,沒有接觸過一點西方經濟學的人是不多的。但是,看看我們的西方經濟學教材,無論是80年代初期的,還是二十一世紀初的最新教材,無論是一般性的教材如《西方經濟學概論》,還是專門的經濟學教材如《勞動經濟學》,每當說到工會時,使人耳熟能詳的是:工會的存在,抬高了勞動力的價格,造成通貨膨脹,阻礙企業經濟的正常發展。不言而喻的含義是:工會是市場經濟的對立面。
說工會抬高勞動力價格,阻礙企業經濟的正常發展,如果是指二十世紀中后期某些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情況,也許是有一定道理的。的確,綜觀20世紀的歷史,(文章來自活動策劃公司、上海公關公司),在不少西方國家,工會力量是太強大了。例如,據統計測算,在20世紀,西方國家勞工所得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斷增加,20世紀上半期勞工所得大體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是50%—60%,下半期則逐步上升至70%—80%。這一結果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工會的努力。
工人收入占到國民收入的70%—80%,企業收入只剩下20-30%,勞動者所得的比重可能是顯得高了一些,對企業和國家的競爭力可能會有不利影響,因此,這些國外經濟學教科書對此進行討論和批評,是十分正常的。
那么,這種對于工會的批評觀點是否符合中國工會的實際?看看我們的勞動者收入就知道了。
關于中國目前的勞動者收入,近期有這樣一個可以類比的數字。據媒體報道,今年1月初,江蘇省副省長吳瑞林在全省勞動保障會議上,公開批評一些企業長期“只漲利潤不漲工資”的現象,指出部分企業工人工資成本僅占企業總成本的4%,甚至低于企業用于公關的費用。由于在我國目前,職工的工資收入就是其收入的主要來源,因此在這些企業,勞動者實際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比這4%高不了多少。
4%多一點對比70%—80%,差距何其巨大。面對這樣的數字,難道我們也能說,我國的工會抬高了工人的工資,阻礙了企業經濟的發展?面對這樣與國外嚴重倒掛的現實,我們的大學教科書,還能照抄照搬國外的理論,抨擊工會的負面作用?在我們的大學課堂,長期講述這種脫離中國實際、漠視工會積極價值的理論,對市場經濟急需的工會觀念的普及,對于社會主義公正體系的建設,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近些年來,我國中央政府的方針政策,是要大力發揮工會的作用,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例如,92年確立市場經濟模式之后,很快就頒布勞動法,修訂工會法等等。但是,勿庸諱言,在我們的許多地方,以投資環境、經濟競爭力為借口,有意無意地抑制工會組織作用,是一個普遍的、不爭的事實。捫心自問,在這些冠冕堂皇借口之后,我們學界人云亦云,從西方國家舶來的工會抬高了工人工資、不利于企業經濟發展的片面化理論,應不應當承擔一點責任呢?
再看看經濟學以外的其他學科。以我們的歷史學(特別是我們的黨史學科)為例。歷史學是我們大中學校教育體系中的基礎課程,對青少年世界觀的形成有重要影響。在我國近現代歷史上,工會是黨領導的一個重要的政治組織,對于推翻舊政權的殘暴、腐朽統治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與此同時,在近現代歷史上,我們也能發現不少工會組織代表企業員工,與企業協商談判,增加工人工資,改善勞動條件的成功事例,例如,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某些企業工會組織。
但是,在改革開放20多年來的歷史學課程中,我們是怎樣向學生傳授的呢?我們讓青年一代了解到“工會的基本職能是通過集體協商和談判,維護勞動者利益”的市場經濟基本常識嗎?恐怕沒有。我們關于工會部分的內容大多是,工會組織是黨領導下的政治組織,是推翻剝削階級統治的工具。毫無疑問,這樣介紹工會組織,在革命戰爭等特殊年代,顯然是符合實際和非常正確的,但是,現在我們黨已經是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執政黨,法律也規定工會的基本職責是維護工人的合法權益,是參與勞資關系協商談判的重要一方,在這樣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的歷史學教科書,難道不應該對工會的作用作更加客觀、全面一些的介紹,以避免片面性對莘莘學子的誤導嗎?
如果通過我們的大中小學的歷史學教材,看到的永遠都是工會組織進行政治性罷工,與資產階級進行你死我活的斗爭,甚至還要奪取國家權力,可想而知,工會組織在我們新一代社會主義建設者的心目中又會是怎樣的形象!這樣的工會形象,政府、社會怎能歡迎,法律怎能允許,我們的勞動者自己恐怕也不愿接近這樣的組織。由此可見,把特殊年代、特殊使命下工會工作形態,片面化解讀為正常化的工作,將會產生怎樣的負面影響。
很顯然,上述問題的存在決不僅僅是經濟學、歷史學,其他的學科領域,例如政治學、法學等,也或多或少存在。指出上述問題,也并不是指責我們的學界、學者思想或者行為有問題,其根本目的是想通過這些現象的描述,提醒我們自己:我國的工會理論嚴重滯后了!它不僅滯后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形勢,更滯后于我國人民對工會這一市場經濟核心機制的迫切需要。十多年立法推行由工會代表工人與企業進行工資集體談判,卻陷入形式主義困境;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在一些企業,工人工資只占企業成本的4%,卻沒有聽到工會的聲音;甚至還出現國務院總理為普通的工人討要工資,等等,這一切都與我們工會理論的滯后密切相關。
面對上述嚴峻的事實,作為學界的一員,我們今天要做的,不是指責企業的貪婪,指責工會組織的無用,指責某些地方政府的短視和糊涂,而是要認真、不斷地反思自己的理論成果,牢記理論聯系實際的工作準則,及時修正、創新我們的理論工作,為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提供更為科學、客觀的工會理論。
十六大報告曾經指出,“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是社會發展和變革的先導”。有了創新的、符合中國實際的工會理論,我國的工會組織才能更好發揮作用,勞動者弱勢的困局才能順利解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才能更加和諧與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