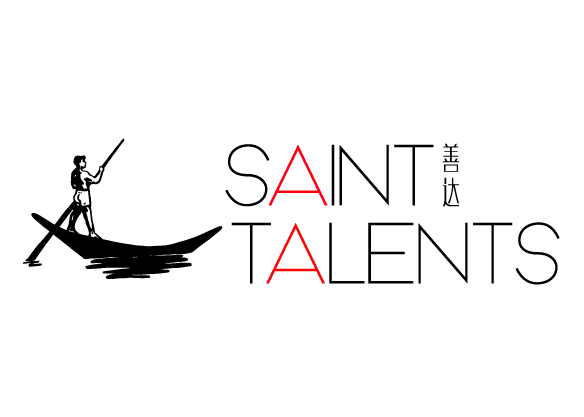總之,獨(dú)特的文化內(nèi)涵與靈活形式和豐富活動(dòng)的有機(jī)融合,完美地演繹出媽鉺信俗的文化軟實(shí)力,實(shí)實(shí)在在地體現(xiàn)出了文化“攻關(guān)”的硬功夫,推動(dòng)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等各方面產(chǎn)生連鎖反應(yīng)。現(xiàn)代公關(guān)關(guān)系與文化底蘊(yùn)的有機(jī)結(jié)合將使得二者相得益彰、交相輝映,從文化公關(guān)的角度審視、營造和運(yùn)作大型活動(dòng),有效地把內(nèi)容與形式統(tǒng)一起來,不僅能達(dá)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還能產(chǎn)生無窮的韻味。
作為一個(gè)重要的公關(guān)推動(dòng)力量,文化在政治經(jīng)濟(jì)上也發(fā)揮過重要的作用。放眼歷史發(fā)展長河,無論什么時(shí)候文化都是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文化是一個(gè)國家和民族遞給世界的名片,也是一個(gè)國家和民族的權(quán)力的象征。今天,人們記住中國、意大利、希臘和埃及,關(guān)鍵是因?yàn)樗鼈冊(cè)?jīng)有過的文化輝煌,它們的文化對(duì)世界產(chǎn)生過重要的影響。縱觀歷史,一種文明實(shí)力的擴(kuò)張通常是與它的文明鼎盛時(shí)期同步發(fā)生,幾乎是與它運(yùn)用實(shí)力向其他社會(huì)傳播價(jià)值觀、習(xí)俗和制度有關(guān)。無論是希臘帝國、羅馬帝國、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還是法蘭西帝國與大英帝國,如果沒有文化優(yōu)勢的運(yùn)用,沒有哪個(gè)帝國能夠繁榮起來。神圣羅馬帝國的發(fā)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gè)文化結(jié)構(gòu)上的帝國野心及范圍的典型例子。
神圣羅馬帝國由約243個(gè)微型國家組成,根本沒有明確的領(lǐng)土輪廓,建立起來的帝國并不單純是一個(gè)軍事機(jī)構(gòu),它還通過文化實(shí)力來施加非官方形式的統(tǒng)治。以世界大同主義者捍衛(wèi)真理的做法為它的“神圣統(tǒng)治”和“羅馬化”披上合法的外衣,為軍事擴(kuò)張行為提供道義上的理由。羅馬統(tǒng)治階級(jí)大力推行帝王崇拜,這不但使統(tǒng)治者及其家族的政治統(tǒng)治合法化,加強(qiáng)了行省居民對(duì)統(tǒng)治王朝的忠誠,而且力圖使被征服者覺得自己是一個(gè)共同的偉大的帝國的一部分,促進(jìn)行省臣民對(duì)羅馬帝國心理上的認(rèn)同和思想觀念上的羅馬化。
羅馬化是指被征服民族逐漸與征服者的行為、風(fēng)俗和生活方式變得和諧一致的一種過程,這一過程是羅馬征服者有意設(shè)計(jì)和精心布局的文化公關(guān)。同化的過程是羅馬帝國在西歐政策的一個(gè)有意識(shí)的組成部分,同化的目標(biāo)是貴族。假如說在羅馬帝國的生活中武力約束和政治統(tǒng)治是絕對(duì)實(shí)情,但是,由于共同文化價(jià)值觀在那些臣服帝國髙壓政治的人一尤其是在精英階層中形成了凝聚力,使得他們并沒有覺察到武力約束和政治順從的強(qiáng)制性。雖然歐洲國家由當(dāng)?shù)卣茩?quán)者實(shí)施世俗統(tǒng)治,但橫跨整個(gè)歐洲的共同文化紐帶是基督教信仰,而基督教的傳播者是一批跨地域的講拉丁語、寫拉丁字的文化精英。在血腥的“十字軍東征”圣戰(zhàn)期間,僧侶體制和騎士體制也作為幫助傳播基督教的跨地域制度發(fā)揮作用。
羅馬的象征性髙壓政治是通過羅馬文明的傳播和文化的公關(guān)來實(shí)現(xiàn)的。愛德華•吉本在他的巨著《羅馬帝國衰亡史》中評(píng)論到:“在距離最遙遠(yuǎn)的那些國家中,羅馬的名字深受敬畏。最兇猛的未開化民族經(jīng)常將自己的紛爭交給羅馬大帝公斷。”羅馬人非常敏感地意識(shí)到了軍事統(tǒng)治和輝煌文化結(jié)合的必要性,那些征服者心里認(rèn)為,帝國的含義中包括共同的信仰和價(jià)值觀念,凝聚力的形成來自共同的文化認(rèn)同。羅馬人很關(guān)注自己的語言在國家行為中的影響,以至于擴(kuò)大拉丁語的使用和運(yùn)用軍事武器一樣,都成為他們最關(guān)心的事情。他們期望通過整個(gè)羅馬帝國普遍深入的文化同化來維持帝國的“神圣統(tǒng)治”。帝國的懷抱包容著眾多的民族,但是他們必須接受超越民族的文化身份。在帝國體系內(nèi),只要少數(shù)民族沒有特定的領(lǐng)土要求,融入“羅馬化”的過程中,他們就不會(huì)受到排擠。“羅馬社會(huì)的順從是一致、自愿、持久的。被征服的國家融人一個(gè)偉大的民族,放棄了恢復(fù)獨(dú)立的希望甚至愿望,幾乎不再會(huì)將自己的存在與羅馬的存在割裂開來考慮。”
可以說,帝國的強(qiáng)盛,國內(nèi)和平、和睦是羅馬人奉行溫和、包容政策的自然結(jié)果,也是在文化上“羅馬化”公關(guān)的成功體現(xiàn)。作為一個(gè)多民族的國家,在歷史演進(jìn)的過程中,中國也發(fā)生過通過文化公關(guān)來實(shí)現(xiàn)政治目的的事件。匈奴自古以來與漢族雜居于黃河流域,在相互交往的過程中也逐漸地受到漢族文化的同化。從匈奴人使用的漢字來看就可以得到證實(shí)。漢朝建立以后就有意地對(duì)匈奴施行漢化政策,漢初婁敬說劉邦與匈奴和親便有此意,婁敬認(rèn)為,漢初天下初定,實(shí)力不及匈奴,必須尋求武力之外的征服途徑。“公主和親”正是這樣一種最有效的征服途徑。他建議劉邦將嫡長公主嫁給匈奴單于,同時(shí)配以豐厚的嫁妝,匈奴在不戰(zhàn)的情況下即可取得榮耀和財(cái)富,一定會(huì)非常稱心如意,從而停止南下侵?jǐn)_邊境,并立長公主為匈奴大閼氏(單于正妻)。其所生之子是大漢皇帝的外甥或外孫,將來會(huì)被立為新的單于,因而匈奴子子孫孫都會(huì)臣服于漢朝。漢文帝時(shí)賈誼也提出“以匈奴之眾為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至遼東,各有分地以衛(wèi)邊,使備月氏、灌窳之變”的設(shè)想和“三表五餌”的建議,實(shí)際上也是想逐步同化匈奴,達(dá)到不戰(zhàn)而勝的目的。從漢匈和親開始,此后歷朝不斷成為中原王朝和親對(duì)象的還有烏孫、吐谷渾、高昌、突厥、吐蕃和契丹等。這些和親之舉,與秦漢以來歷朝歷代不斷修筑長城一樣,都是當(dāng)時(shí)的統(tǒng)治者面對(duì)來自北方威脅的戰(zhàn)略防御之策。但就實(shí)際社會(huì)政治效果而言,和親遠(yuǎn)勝于修長城,文化公關(guān)的魅力遠(yuǎn)大于軍事戰(zhàn)爭的效力。“和親”是中國和合文化的外在體現(xiàn)方式,向世人展示出其開放性、包容性的特征,體現(xiàn)著中國文化的成熟和智慧。它既能“化干戈為玉帛”,解決民族糾紛,又有效地促進(jìn)了民族間的大融合。對(duì)于促進(jìn)中華民族的形成、發(fā)展和統(tǒng)一做出了積極的貢獻(xiàn),兩千年來一直為歷代各族人民所稱頌。從歷史實(shí)踐上我們也可以看,漢唐實(shí)行和親不損其強(qiáng)盛,宋明反對(duì)和親不減其羸弱。
史書記載,“(漢)元帝以后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漢書匈漢傳》)昭君作為“民族友好使者”出塞之后,胡漢之間50多年友好相處,北國邊疆出現(xiàn)了“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無干戈之役,人民熾盛,牛馬布野”的和平景象。昭君出塞、胡漢和親作為歷史上一種文化現(xiàn)象化干戈為玉帛”,實(shí)現(xiàn)民族之間“雙贏對(duì)話”的中國方式,為“華夏一統(tǒng)、胡漢一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chǔ)。今天的內(nèi)蒙古早已成為“模范自治區(qū)”(周恩來語),不但因?yàn)檫@里是昭君出塞、蒙漢和親的地方,是王昭君的長眠之地,更因?yàn)樵谶@里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千萬個(gè)現(xiàn)代版的“王昭君”。新中國成立之后,黨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各族人民和諧相處。在不同的國家建設(shè)時(shí)期,,千百萬漢族青年來到祖國的北部邊疆,與當(dāng)?shù)厝嗣窈椭C又友好地工作生活在一起,并在這里“扎根、開花、結(jié)果”,用事實(shí)有力地說明了“漢族離不開少數(shù)民族,少數(shù)民族也離不開漢族。”如今,“昭君文化”更是已經(jīng)成了呼和浩特市的文化品牌。自1999年以來,呼和浩特市每年舉辦一次“昭君文化節(jié)”,這些既說明和親文化影響的持久性,也說明文化公關(guān)具有現(xiàn)實(shí)意義。
關(guān)鍵詞索引:文化,“羅馬化”,公關(guān),成功,體現(xiàn)
|